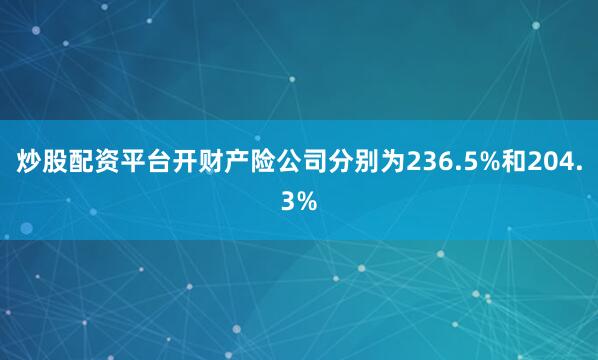“1949年4月18日凌晨两点,周恩来放下电报,抬头问张治中:‘文白,天快亮了,长江也快亮了,你还要回南京吗?’”昏黄灯光下,六国饭店客房里只有纸墨的味道和墙上钟表的滴答声。张治中把手中的礼帽抓得很紧,回答得干脆:“我是代表团团长,不回去,怎么向李副总统交代?”一句话,既带倔劲,也含无奈。

这场纠结其实从三个月前就埋下了伏笔。年初,蒋介石宣布“引退”,李宗仁接掌大局,南京高层瞬间成了散沙。白崇禧极力主张和谈,眼光全落在对延安“熟门熟路”的张治中身上。面对兰州与南京两头来电催促,他心里清楚:此行是救火,更是走钢丝。沉吟数日后,他还是捧起公文包踏上东去的列车。
抵京前夕,他又拐到溪口向蒋介石“辞行”。在奉化小楼里,老蒋一面翻报纸一面淡淡丢下一句:“去吧,苦差事,注意安全。”听来像鼓励,实则一句空头支票。张治中却将这番话写进演说稿,想借“委员长愿意和平”来压一压顽固派的火气。屈武在机舱里提醒他蒋经国的冷嘲——“太天真”。张治中脸色铁青,却也无计可施。

4月1日,北平机场风沙大,周恩来没有现身欢迎,张治中心里咯噔一下。进城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横幅:“欢迎真和平,反对假和平!”那一刻他悟到,自己在两条战线上谁也讨不到便宜。傍晚碰面,周恩来没有寒暄,开门见山:“既然谈和平,为何还去奉化听战犯指示?”张治中解释自己只是探底气。周恩来毫不松口:“只要蒋介石还能挥手示意,这桌棋就下不成。”两人僵坐半小时,气氛像晚春的北风,硬。
之后的正式会谈,周恩来详细陈述八项条款:惩办战犯、跨江作战、接受人民监督……张治中提出四十多条修改意见,中共方面采纳一半。谈判桌上,黄埔同窗互敬茶水,却刀来剑往。张治中以兄弟比喻国共关系,周恩来严肃回击:“不是兄弟斗嘴,是人民与反人民的较量。”话锋之利,让旁观者都替张治中捏汗。

4月15日晚,定稿摆在桌上,南京必须在17日前给答复。张治中犹豫到凌晨,终究拍电报回宁。“拖到20日之前必须渡江”这句硬话,还没等回复落地,百万大军已悄悄集结岸边。18日凌晨,周恩来收到前线最新坐标,他把电报递给张治中:“江面雾薄,船已下锚。”张治中沉默,握笔的手有些抖,却依旧坚持返宁:“我若不回,被说成投共,李副总统难做人。”
20日凌晨,南京政府回电拒签,江北炮火同时拉响。长江天险不到一昼夜被撕开两百公里口子。听着外头礼花似的炮声,张治中脸色灰白,他不是不知局势,而是不肯放弃最后的儒将体面。他推开窗,北平城夜空安静得出奇,只有几声挑灯夜行的车马。周恩来再次登门:“西安事变,我们已欠一位张先生;今天不想再欠第二位。”这句话戳在心口,张治中坐在椅子上许久没说话,最后吐出四个字:“再让我想。”

他真正下决心,是因为家人。南京方面已贴出“叛逆名单”,张家人危在旦夕。周恩来派地下党绕道上海接应,把张治中的夫人、孩子和几位亲属分批送到北平。四月末,张治中被半哄半请赶到机场,当看到妻儿从机舷阶梯走下时,泪水突然涌出——“恩来先生,这份情我还不起。”周恩来拍拍他肩:“留下,才算还。”
不久,南京派来的专机盘旋北平上空,塔台回答“跑道维修”,对方只得返航。电讯里谩骂声不断,张治中索性登报声明,表明自身去留选择。外界风声越烈,他越冷静;有朋友劝他“划清界限”,他只是摇头:“我仍是国民党员,但先是中国人。”

五月,解放军接管南京,江南战事迅速收尾。北京饭店里,周恩来递上一份名单,请张治中出任新政协筹备委员。张治中起身敬礼:“我资格浅。”周恩来笑,说毛主席的原话:“过年三十已过去,初一该一起干活。”张治中沉吟片刻,接过文件,郑重签字。
二十年后,1969年4月6日。张治中病逝北京。统战部有人提议不举行仪式,理由是“非常时期”。周恩来当场否决:“必须送一程,我们不能对不起他。”灵堂布置简单,却挤满了老战友、老对手。花圈簇拥中,黑底白字的挽联并不华丽:一生尽瘁求和平,半世奔波护苍生。这两个短句,道尽了张治中从黄埔学员到人民政协副主席的漫长折返。

回想1949年那个凌晨对话,长江的雾早已散去,而“不能对不起你”这句话,却被许多人记在了心里。这或许就是那一代政治家的分量——立场可以不同,诚信却要顶天立地。
金河配资-在线实盘配资-线上炒股配资-股票杠杆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专业股票配资门户当日最高报价12.00元/公斤
- 下一篇:没有了